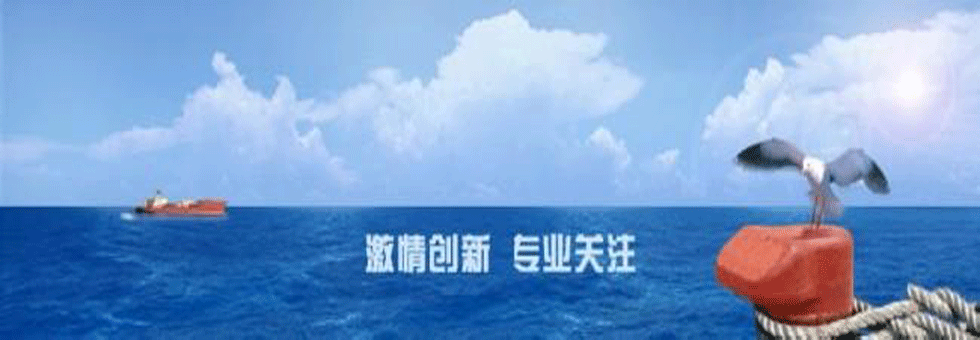
北京哪里能治愈白癜风 htt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昨天看到一篇关于《舌尖上的中国》的智障文章,节选其中的两端神论:
就在这两天,因为黄馍馍而成名的靖边县的老黄被西贝莜面村的老板叫到了北京,准备弘扬光大西北美食。听到消息后,胡迎迎非常生气,她说她打电话把那个老板骂了许久。她就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商业化的现实,在她心目中,老黄就应该在山崖上充满自信地做他自己唯一的黄馍馍。”
“主食的一大趋势是工业化。在嘉兴的五芳斋拍摄包粽子的画面,胡迎迎印象深刻的是,尽管还是靠手工,可是工人们已经机械得如同机器。最能干的工人,一天能包数千个粽子,劳动力本身的低廉价格,使得这种手艺也并不太受尊重。她说自己心里很不舒服,有人一天包个粽子,旺季包个。一辈子包这么多的粽子,意义何在?”
就是这篇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微博搜一下,不过满满也是槽点不看也罢。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朋友素质也是高:
槽点太多,真不知道如何吐起。现在众多脑残的城市小布尔乔亚们总喜欢发出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无病呻吟”,天生的对“工业化”名词有一种抵触感。用赵丽蓉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吃了几天饱饭,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他们如此向往“自然”如此向往“田园牧歌”,但你要让他们去个没wifi没空调的地方,几天都住不下去。都是工业化惯出来的矫情病,要不农村的猪圈旱厕了解一下?
这篇文章就反应了《舌尖上的中国》存在的核心问题,第一季还好,从第二季第三季开始就有点走火入魔了。总感觉剧组很愚昧地认为,“天然”的就是好的、“手工”的就是好的、“古旧”的就是好的、深山老林和农村的就是好的,以至于台词中频繁出现“古法”“匠心”等词语,仿佛某白酒的广告。甚至就是一个“回坊”都要罔顾史实,强调“唐朝时就已形成”“至今保留着当年的格局”;还有什么“土色的碗,配红色的红烧肉”等等这是病,而且病入膏肓。还有类似这种神论:
我上大学的时候专门参观过景德镇的烧瓷车间,我还记得车间师傅提起过,要烧制的陶模里非常忌讳有气孔,否则很容易烧出残次品,如鼓泡、开裂等。所以说没有气孔是好事啊,尼玛泥里的气孔=呼吸=有泥性=有人性,这尼玛是何等的智障。我生怕这个节目播出之后社会上开始对文科生有偏见了,我再次一定要替所有文科生们澄清一下:这尼玛就是蠢,冒气泡的蠢,跟学文学理没关系,我们文科生也是有科学素养的,好歹也是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
今年一月初,马前卒先生在上海有一场演讲《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这个视频在B站就有,大家有时间了可以去看看,里面讲到了柳州螺蛳粉、武汉热干面、河南烩面等几种美食的起源。关于螺蛳粉的起源,有说是工厂食堂给夜班工人提供夜宵发明的;有说是工人电影院散场后大排档老板为了迅速煮粉发明的;有说是很多外地人半夜下火车要吃饭,小店老板只剩下螺蛳汤和米粉,临时拼凑出来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螺蛳粉肯定不是什么古代食品,也不是家庭厨房里面的创造,而是现代餐饮企业为了快速批量制作而发明的快餐。
马前卒先生分析地很好,因为螺蛳粉有大规模“工业化”的潜质:首先,它用的是干切粉,不是湿粉,主要原料好运输;其次,把螺蛳预先煮化在汤里,油水和味道很足,便于快速制作油水很足的热汤粉;第三,配料是腐竹、酸笋、酸菜、花生米,和一小把青菜,大多数配料比较耐储存。这几条优点都接近于方便面。所以,柳州螺蛳粉占领全国市场,一半是靠开店,一半是袋装的方便面式销售。柳州卖给全国的袋装螺蛳粉,去年销售额超过30亿。
那么这一曾经火遍全国的美食有多么的“传统”呢?其诞生大致在七十年代左右,寿辰不超过四十年。但是即便没有“传统美食”这个光环,也丝毫不影响螺蛳粉的美味。同样,河南烩面,年出现在郑州,是饭店公私合营之后,为了批量制作热汤面而发明的。武汉热干面,是年左右发明的,饭店老板每天做面条的半成品,做少了不够,做多了会粘在一起,他就想办法在面条上拌了一些油和芝麻酱,结果大受欢迎。可以看出,螺蛳粉、热干面、河南烩面,这几种食品的共同点是工艺简单,可以预先储备大量半成品,随着市场需求快速制作。这就是工业化的美食啊,这就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产物。
还有一个例子,中国四大名鸡:德州扒鸡、河南道口烧鸡、锦州沟帮子熏鸡、符离集烧鸡——每种鸡对应一个近代铁路要地。原料都是鸡肉这种最廉价的肉类,同时烧鸡含水量低,容易携带,能长时间保存无论是路途中边喝酒边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四大名鸡和螺蛳粉、热干面等特色美食一样,都是中国工业铁路时代的产物。
但是很遗憾的是,大多数人一边享受着工业化提供的便利,一边没有走出“崇古”“复古”的思维误区,这也导致了一些食品为了迎合市场不得不给自己“贴金”。典型的例子,“乾隆下江南”养活了上百种小吃的历史,而仔细追究起来这些小吃大多形成于解放后甚至于改革开放后这几十年。河南的王守义十三香诞生于年,几千年来,因为交通不便,香料只要离开产地,到别的气候带都是奢侈品。建国后武汉长江大桥打通了京广铁路,第一次把中国南北连接起来,北方人也能廉价获得南方香料了,所以在京广线上的驻马店出现了廉价的混合食品香料。当然王守义家族不承认这一点,坚持说自己的香料配方有上千年的历史,然而有较真的网友考证过,其中许多香料在宋代甚至明末才传入中国,何谈千年之久。然而这无所谓,讲一个“崇古”的故事不妨碍几块钱一包的十三香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走进千家万户,为我们餐桌上增添美味。不过我们要感谢的不是流传千年的配方,而是现代便利的交通和工业化生产。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美食也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比如《红楼梦》中这一段描写非常生动:
凤姐儿听说,依言搛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果又搛了些放入口内。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象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签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刘姥姥也算是一方大地主,但是她活这么大也无福消受这样的美食。古代没有味精,能提供鲜味的东西只有老母鸡和海鲜熬的浓缩汤。普通的人家和饭店用不起这么昂贵的调味料,只有以山东孔府菜为代表的高端鲁菜才会用足够的母鸡汤和海味来制造美食。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明确啊,我就是个无产阶级,我又不是帝王将相我也不配姓孔,所以我感恩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能让我每顿饭都能通过廉价的味精尝到谷氨酸钠的味道。
在封建时代,甚至于我们建国后不久的农业社会里,普通人是没有资格讲“美食”的,只有吃饱饭才是天大的道理。马前卒先生在演讲里说过他去辽宁营口的一个故事,当地人说,60年代粮食不够吃,最穷的人家才去海边搞点虾爬子(皮皮虾)。为什么穷人才吃皮皮虾?因为皮皮虾的热量和脂肪含量都很低,在没吃饱之前去捞皮皮虾,耗费的能量得不偿失。饥荒时只能吃大闸蟹的江南人也是同一个道理。
在那个时代,稍微条件好一点的人吃什么食物?最好的美食就是粮食、油脂和盐的组合,典型的例子是猪油拌饭。只有社会发展了,每个人日常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有了充足的保障,皮皮虾和大闸蟹才能称之为“美食”,否则它们才是无法供养人的“垃圾食品”。
单不要说工业化的化肥、农药给粮食产量带来了多大的提升、养活了多少人口、在曾经的中国农村,炒菜都是奢侈品。因为无论是油还是燃料,都供应不充足。炒制的食物要比其他做法需要更多高的温度、消耗更多地燃料。所以各地真正能追溯到几百年前的民间菜系,主要就是炖菜,比如东北的猪肉炖粉条。所以说我们要感恩现代化生活啊,赞美工业化。别说这个了,之前城市供应大白菜是国家领导人要过问的大事。像我们这些90后还都对小时候每到冬天屯大白菜,有很深的印象,这才过去多少年啊。
在我心目中,最完美的“手工匠人+工业化”的融合是老干妈。年的前一年,老干妈陶华碧用捡来的砖头和石棉瓦,搭成一间不足10平米的凉粉店。看新闻报道里写:“开业第一天,陶华碧只卖出7斤凉粉,没想到凉粉的免费佐料——她自制的风味豆豉辣椒酱,却被食客们抢光。老干妈的名号很快在附近的高校学生中叫响,再由来往的大货车司机传遍云贵。”划重点了啊“高校学生”“大货车司机”哪一个都是现代工业化成果,而老干妈也积极地拥抱工业化:
看《每日人物》里有一篇报道,酱老干妈厂对员工的福利待遇也是首屈一指:管吃管住,普工薪水至少超出当地平均水平块。老干妈把员工看作自家孩子,还曾主持员工的婚礼,有位保安得重病要透析,陶华碧知道后当即签字拿钱,嘱咐“别在乎钱,治好为止”。老干妈还不搞资本运作,不上市不贷款不融资,不炒作不做广告,二十年缴税几十亿,真·社会主义之光啊。
诚然,工业化有工业化面临的新问题,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比如环境保护问题。但是这需要更完善的管理和更先进的制度去规范,我们是要向前看、朝前走,而不是说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去渴望着复古、去工业化,把落后当成追求的目标。
但是,现在又更让人恶心的,就是这群城市小资产阶级包裹在内核深处一种浓浓的优越感。就像上文这位《舌尖上的中国》的编导一样:“在她心目中,老黄就应该在山崖上充满自信地做他自己唯一的黄馍馍”——你TM是谁啊!凭什么人家就得在贫瘠的地方做一辈子黄馍馍啊!潜意识里这群垃圾就把手工劳动者看做了“下等人”,认为这些人就只配做这种生活,只配为我服务,只配为我抒情做素材,并主观给“下等人”的人生做了安排——做你一辈子的黄馍馍吧,不然我们这些小布尔乔亚上哪去抒发感慨、上哪去无病呻吟呢?
我想起了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有一次爬凤凰山,半路遇到了几位香港的远足爱好者,就一起结伴而行。走到一处,一位香港朋友介绍说,这个地方本来有一对老夫妇卖山水豆花,据说卖了三十多年了,就是用的纯天然的山泉水,超级好吃。但是前几年听说他们在市区买了房,不来这里卖豆花了,可惜以后吃不上了。结果同行的几个SB就开始感慨,说什么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卖豆花的都丧失了初心,怎么就去市里买房不干了呢;山上卖豆花赚了我们这么多年的钱,说不干就不干,让我们这些旅游爬山这么累、想吃豆花的、闪闪发光的年轻人们多遗憾啊;三十年的事业就这样放弃,可见理想在金钱面前一文不值啊。当时就把我恶心坏了,这TM都是什么东西啊。人家干了一辈子了去买个房养老怎么了,合着就得在山上窝棚里住,退休都不给,就给你们做豆花就对了啊。说白了就是一群SB的谜之优越感,根深蒂固的歧视,觉得你就配作这个,我对你的赞美、购买你的产品,是对你最大的肯定,你是无上的荣光。
还记得《纸牌屋》里木下总统和他“最好的平民朋友”——那位做肋排特别拿手的黑人厨师吗?但人家是真·大资产阶级,有这个毛病也就算了。结果这种优越感我发现在脑残到冒泡的小资产阶级中更加普遍。还是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一次学术活动,吃免费自助餐的时候(惭愧,其实我一大半是冲着这个去的)跟两位德国人和两位芬兰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来了,这四位朋友都是港中大的交换生,必须要承认他们素质很高,言谈举止也很得体。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总结了一个很普遍的规律,不管多么理智多么客观的西方人,一到西藏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观点绝对脑残——从学生到教授,非常普遍,屡试不爽。这几位也是,一个德国人就说么,西藏的传统被破坏了啊,信仰被玷污了啊,历史被遗忘了啊,藏民好可怜啊balabala
当时我就火大了,我连烤肠和蛋糕都顾不上吃了,直接就喷起了德国人,我说:“Fuckingyourstupidtradition.WhynotTibtansdsrvabttrlif?Whynotthydsrvadvlopdsocity?WhynotTibtansdsrvusingipadandlivinginairconditionroomlikyourEuropansinstadknlallwayonthroad?Whynotthydsrvfactorisschoolsandmodrnhospitalsinstadgivingthirliftimin